14岁又298天的王宁攀(化名),死在了工厂几百米外的出租屋床上。被同事叫做小攀的他,同母亲一起在广东佛山的这家内衣厂打工,因身份登记信息显示未满16岁,王宁攀被打上“童工”的标签,他的死,也难免让人对其工作环境和强度有所猜测。在湖南,有不少像王宁攀一样未成年即辍学出来打工的孩子。(《新京报》5月9日)
一个不到15岁的童工猝死在出租屋床上。无论如何,都是突破一般人生活经验而又让人心酸的悲剧。更应该正视的:这类悲剧还不仅仅是个体性和偶发性的。记者通过探访王宁攀家乡发现,这类从学校辍学而提前“混社会”的“童工”并非少数。去年有媒体报道,国家社科基金的一个课题组深入西部一个偏远村落,微观揭秘了乡村底层孩子们所不为外知的日常“江湖”。而这个“江湖”与此次记者调查发现的,乡村底层留守儿童沉迷于网游、表现出强烈的厌学情绪,多有相似之处。由此可见,王宁攀的个案虽属极端,但其背后对应的留守问题却真实而普遍。
在记者探访的王宁攀家乡的儿童生活状况中,迷恋网游和被留守,是当地学生过早辍学、普遍厌学的两大主因。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乡村学生迷恋网游可能与被留守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内在联系。在上述田野调查中,调查者发现,一些留守学生由于缺乏心理上的安全感,往往会通过拉帮结派来结成共同体。当地网吧管理松弛,大开方便之门,说留守儿童从网游中寻求一种虚幻的安全感或并不算虚言。从网吧对未成年人的照常开放,到对学生出入网吧只剩老师与他们徒劳地“打游击”的现象,不得不让人追问:那些要求建立的对留守儿童的公共干预机制,到底在哪?
年近15岁的王宁攀及其同龄人,正是新一代留守儿童的典型代表。相较于他们之前的留守儿童,这一代人更多地接收外界信息,通过互联网对外部世界有着更直接认知。他们受到外面世界更多的物质诱惑,急于走向社会,寻求自由、独立,这种诱惑很难转化为向上的决心和行动。因为学历文凭相对“贬值”,在“读书无用论”再度上升的现实背景下,辍学外出“淘金”,成为一种更“现实”的选择。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当我们用社会整体向前发展的尺子来衡量留守儿童的生存境遇和未来前途时,往往可能是不准确或失真的。这些在课堂上越来越坐不住的乡村少年和留守儿童,真能比他们的父辈拥有一个更体面的未来吗?
注意到一个细节,在谈论童工现象时,虽然当前招聘童工已明确为非法,但一些企业仍铤而走险。除了用工成本上的诱惑,这次媒体报道中,一企业负责人所透露的信息或许展现出一种被忽视的视角:“不可否认,暑假期间,小孩子没地方去,在家里大人不放心,我们厂的家长带孩子过来,不好拒绝。”从往日留守家庭孩子与父母的“一年一见”,到现在放假了可与父母以打工的方式团聚,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说是一种进步。这些留守孩童虽然有了更多的机会踏入城市,却仍只能以一个“打工者”的身份来立足,留守与身份隔阂的代际传递,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观。
无论是现实上演的悲剧,还是各类调查所呈现出的乡村底层少年与留守儿童的“原生态”,留守的话题正在被越来越多地提及。从留守儿童自杀到童工之死,这些都可以说留守问题的一种延伸和外溢。而王宁攀死在了远离故乡的出租屋床上,更像是一道隐喻:随着时间的推移,足以说明留守问题所带来的社会后遗症必然会愈加显现,并带来更大的溢出效应。这个群体,留守于乡村,却必将流入城市。关键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是想象中的“鲤鱼跳龙门”,还是像浮萍一样提前“混社会”?王宁攀的遭遇,则表现了一种最坏的情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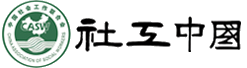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