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对于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变迁而言,是其制度变迁极其重要的一个历史关键节点和否决点。因为这一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628美元,由此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也就说意味着中国已具备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经济基础;这一年中国城乡人口比重分别为49.68%和50.32%,此后中国迈入城市人口比重超过农村人口并不断提高的新阶段。
换言之,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改革深化等带来了经济、社会、人口等深层结构的变迁,相伴而来的发展机遇和社会风险则同时增加。面对复杂国际形势和国内情况,国家自2010年始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福利与民生建设的制度与服务供给。有学者甚至将2010年界定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与儿童福利制度“元年”,认为我国已由残补型社会福利制度转型到适度普惠型福利制度建设的新时期。
2010年至今,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社会政策和具体措施,足见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与转型的力度和速度在不断增强。2012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创新”,拉开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序幕,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意味中国将进一步强力打破原有“强国家-弱社会”格局,逐步转向培育多元社会主体,构建“小政府、大社会”与多元主体共治共享的新社会格局。
在此背景下,培育社会组织自然成为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文化繁荣、生态保护的迫切时务。因而,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在国家政策驱动和政治动员下,各类社会组织得到快速发展,并在社会治理与社会服务中的作用不断提升。特别是城乡社区服务类、公益慈善类、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社会组织在政府加大登记注册程序简化力度后呈雨后春笋般疯长之势。
为什么要重点培育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呢?其根源还在于社区对于民生建设与社会治理有着不同寻常的作用和功能。社区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是人们赖以生存与生活的载体,她为型塑社区居民(村民)的共同心理、文化、信仰结构和生活与生产方式提供养分和土壤。诚如滕尼斯1887年在其《共同体与社会》所言,社区是一种“建立于本质意志与自然情感基础上的共同的生活方式”。
因而,自1986年民政部倡导社区建设与社区服务以来,国家对于社区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特别是在近年社会治理创新战略指引下,社区成为社会治理最为基础和核心领域。社区上接政府,下联百姓,政府绝大部分政策和服务都通过社区传递给百姓及其家庭。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国家将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作为推进社区治理与民生发展的基本模式在全国全面推开。
据民政部数据显示,2010年底全国共有各类社区服务机构和设施15.3万个,其中社区服务中心12720个,社区服务站44237个;城镇便民、利民服务网点53.9万个;社区志愿服务组织10.6万个。到2015年底全国共有各类社区服务机构和设施36.1万个,其中社区服务指导中心863个,社区服务站12.8万个;城镇便民、利民服务网点24.9万个;社区志愿服务组织9.6万个。从这组数据变化来看,中国基层社区组织得到快速发展,也就是说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取得卓越成效。在欣喜之余,值得反思和讨论的是当前基层社区组织培育的路径问题。从观察来看,具有以下三种路径:
一种是自由生长。互助与合作是社区关系与功能的基本特质和功能。虽然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在持续加速推进,但其农业文明和农民社会的社会本质依然没有完全改变,因而乡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关系网络依然广泛存在和有效运行。也就是说无论在农村社区还是城市社区,即使在市场经济理性,以及人口流动潮流与征地拆迁运动下受到严重冲击,但社区中的非正式自助、互助与志愿精神是长期存在的。因而建基于互助与志愿精神、社区与群体共同文化等的非正式自助、互助、志愿、公益组织在中国社区中也长期存在并有所发展。比如,近年来火爆的广场舞,其背后是一个社区居民基于共同心理与兴趣、共同需要与文化所形成的不同形态的自助或互助组织形态。
常见社区中一些人们相聚在一起开展起舞弄剑、下棋品茶、吹拉弹唱、登山郊游等各种活动,其实质也是一种非正式社区组织。这样的非正式组织没有既定和明确的组织章程、活动形式、组织目标、人员构成,但极具活力和生命力。近年来国家加强社区活动中心等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和投入后,进一步改善了社区居民开展各类自助与互助活动,有助于发展和培养植根与社区的自助与互助组织。如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在其金牌村和车田村等乡村社区于2016年发起主题为“共建共享,打造我们的幸福家园”的“屋场”建设运动,由镇政府投资保护古树、古井、古屋等,对社区中的楼、牌、屋、亭、桥进行美化,刷印和张贴与传统文化、村庄历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有关的名人名句名画等,引导村民形成“邻里相助、幸福一家”的社区互助和志愿精神。
同时因地制宜倾力打造综合社区活动中心和社区服务中心,面向老年人、儿童、妇女、青少年和普通村民等组织各种群体性文体活动,针对单亲家庭、困难家庭、流动人口家庭等发起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经过一年多努力,这两个村形成了数量可观的不同类型的群体性、志愿性组织,大大激活了社区活力和幸福感。
一种是进笼规养。近年来,全国各地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和公益慈善组织培育中引入“公益创投”机制,由政府、企业、基金会等为主体参与提供资金,培育和支持初创期和中小型社会组织发展,以提升其社会服务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在国家逐步强化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于社会服务过程的主体性和规范性,因而在公益创投项目申请和政府服务购买项目申请的资格准入机制上逐步由非正式组织“范进”向正式组织“严控”转变。
在具体实践中,可以看到各地在初期启动公益创投和政府服务购买项目活动时,对于申报组织的资质要求相对比较宽泛,资助对象可以是项目团队,也可以是服务机构。也就是说对于申报者是否具有正式组织身份和资质并不受到严格限制。这样激活了社区服务项目创意和参与意识,促使一些自助性、互助性、志愿性非正式组织通过参与公益项目申报与运作来提升其服务能力和发展能力。当社会组织培育达到一定规模和数量后,培育目标则转向以培育正式组织为主导目标。因而,在公益创投项目与政府服务购买项目申请资格上基本规范为正式登记注册的组织。
由此一来,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走向“进规喂养”方式。为何如此呢?其根源在于资源主要由国家控制,社会组织又囿于其公益性属性而不能采取商业利润运营模式,社会捐赠意识薄弱,社会组织筹资能力偏弱。因而社区社会组织当前只能主要依靠政府资金支持来发展和开展服务。比如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2012年底仅有1000家,到2016年底已发展到5880家,虽然数量增长迅猛,然而因为资金来源不稳定等因素影响,出现不少“空壳机构”和“僵尸机构”。如何打破这种发展瓶颈,是值得从制度设计和组织治理角度更深入的探索和创新。
一种是强弱相争。社会组织培育必然要经历一个由“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由“鱼龙混杂”到“专业培植”的转型期。社区社会组织数量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所面临的便是“生存竞争”和“优势发展”课题。因而,国家在推进社会组织培育过程中,其策略也是一个由“粗放型”准入到“规范化”培养的过程。在努力培育到一定数量和规模时,政府再通过政策规范、资金配置、竞争引入等方式让社会组织进入一种竞争发展、规范发展和持续发展的生态中。
当前社会组织申请分为区(县)、市、省和民政部四级平台,依据国家政策引导,主要通过引导社会组织在区(县)注册登记来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但社会组织无论在哪里登记注册,它都如企业一样具有在全国活动的合法性和主体身份。因而当前各级政府、各系统在公益创投项目、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等委托、购买和申请过程中并未或并不能对社会组织登记属地有明确限定。同时政府作为委托方,基于理性和效益考量,越来越注重受委托方社会组织的综合实力和服务能力。因而,在一些地方的项目申请和购买过程中开始出现不同规模和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与社区社会组织进行严酷的“强弱相争”局面。
比如一些城市出现在岗社工人员超千人,超数百人的“大型”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与在岗人员不足十人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同时竞争项目和其他资源,因而强势机构自然能在项目申请和政府合作过程中彰显出强劲的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并可能“雄霸天下”和“独领风骚”。由此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就开始凸显,一些弱势社会组织和初创期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和资源空间也由此受到强势社会组织的严重挤压。如何构建一个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和“竞争发展”环境,已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课题。
本文作者冯元,湖南长沙人,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工作博士生,中级社会工作师。现为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教师,兼任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南京市共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社会工作。曾获“2015年度全国百名优秀社工人物”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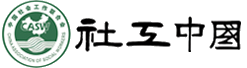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